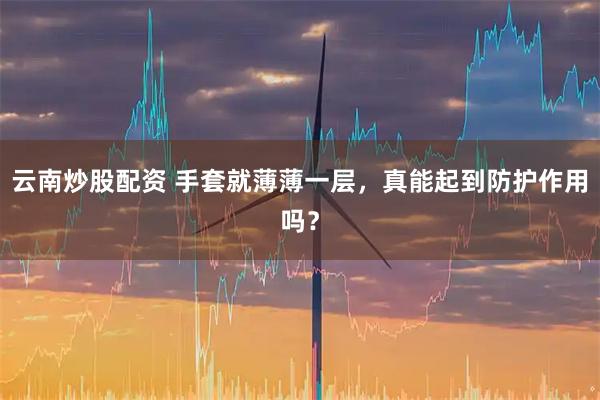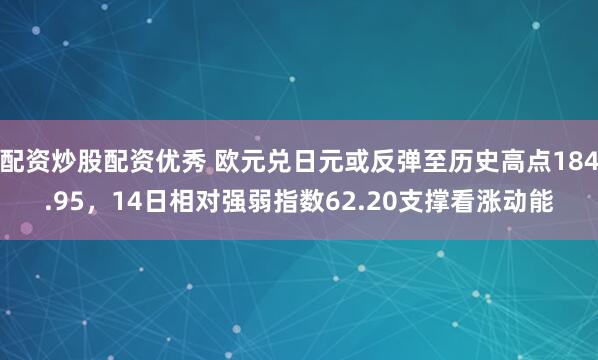在沈阳的一家超市货架前,一个朝鲜留学生站了十七分钟,只为选一包方便面。七种口味,让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 在平壤,只有一种印着“黎明”商标的白色包装,面条是直的,调料包里只有盐和味精。 而在这里,红烧牛肉、老坛酸菜、香菇炖鸡连吃什么都成了需要动用意志力的难题。

我跟你讲,这不是在矫情。 你每天在三十个外卖选项中划来划去最后点了常吃的那家,本质上和她没什么不同。 只是你习以为常的“选择权”,对她而言,是一场颠覆世界观的头脑风暴。
一、 当“无限选项”成为日常酷刑

她叫金玉珍,来自平壤。 出国前,她的人生是一条精确的流水线:早上六点广播起床,七点集体早餐,八点上课,晚上九点熄灯。 像一颗标准零件,严丝合缝。 她出国前,母亲的叮嘱是:“到了那边,别人给你什么就吃什么,别挑。 ”
可问题来了,这里没人“给”。 一切都得自己“选”。

第一次进ZARA,她以为进了宫殿。 不是因为豪华,是因为那些衣服就那么挂着,任何人都能摸,能试,能穿上身照镜子,然后说“不要了”,再挂回去。 在平壤? 购物是项仪式。 你得先在柜台看样品册,选定款式尺寸,付款,等营业员从仓库取来。 不能摸,不能试,买了就是承诺。 而在这里,承诺像试衣间的帘子,可以随意拉上又拉开。
更冲击的还在后面。

她的中国室友小敏,在商场试了八条裙子,每条都拍照,发给了微信里三个不同的男生。 玉珍坐在外面的长椅上,手指无意识地绞在一起在平壤,一个女孩同时和三个男生暧昧,是要被送去进行“思想改造”的。
小敏最终一条都没买。 那条399元的红裙子,被留在了试衣间挂钩上,像一段被试穿后又放弃的爱情。 回去的地铁上,小敏刷着手机笑出声:“三个都回了。 学长说好看,男朋友问是不是太露,小奶狗发了爱心表情包。 ”

“那你选哪个? ”玉珍小心翼翼地问。
小敏抬起头,眼睛亮得惊人:“选? 我为什么要选? 都吊着呗,看谁表现好。 ”

玉珍转过头,看着窗外飞驰的广告牌。上面写着:“年轻,就要拥有无限可能。 ”她第一次如此具象地理解,“无限可能”意味着连爱情都可以待价而沽,可以“试用”,可以多线程操作。 这不是道德问题,这是运行规则的彻底不同。
二、 被瓦解的秩序:时间、记忆与“自我”
如果说白天的冲击还停留在表层,那么夜晚的遭遇,则直接动摇了基石。
某个凌晨一点,宿舍已熄灯。 她听见下铺的小敏打电话:“对,老地方,麻辣烫多加辣,奶茶要波霸,半小时能到吗? 行,给你加五块小费。 ”
半小时后,敲门,扫码,付款。三十秒,热气腾腾的夜宵就摆在面前。
玉珍躲在被子里,心跳如鼓。 在平壤,夜晚属于国家。 九点宵禁后,街道上只有巡逻队的脚步声。 半夜吃东西? 要么你是特权阶层,有私人厨房;要么你在做违法交易。 而在这里,一个普通女大学生,花28块钱和半小时耐心,就能合法地打破“夜晚的秩序”。
更让她世界观裂缝的,是那“五块钱小费”。 这意味着,服务可以因为“更好”而获得“更多”。 在她的祖国,报酬是固定的。 工厂工人3000朝元,教师3500朝元,医生4000朝元。没有奖金,没有小费。 平等,意味着无论努力与否,结果都一样。 而这里,努力被明码标价,成为可以浮动的价值。
但最寒冷的一击,来自她自己的手机。
她在图书馆拍了一张很美的雪景:一个男生在给女朋友系围巾。 拍完,她习惯性地打开修图软件。 调整亮度,加滤镜。 然后,她发现了“消除笔”。手指划过,男生消失了。 再划,女生消失了。 继续划,雪花、树木、建筑全部消失了。 屏幕只剩一片刺眼的白。
她盯着那片白,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冷。如果记忆可以像擦除笔迹一样随意删除,那什么是真实的? 如果过去可以一键清空,那我们是谁?
她想起平壤家中客厅的墙。 三代领袖的照片挂在那里,每天早晨都要擦拭。那些相框不能移动,不能更换,不能质疑。 它们是记忆的锚,把一家人死死固定在历史和国家的坐标系里。
而现在,手里这个小小的机器告诉她:没有什么是不可删除的。 包括你自己。 这种自由,令人战栗。
三、 一场关于“浪费”的笨拙起义
学期结束前,玉珍决定做一个实验。 她去了小吃街十字路口,决定进行一场“全错误选择”的消费:
第一步,麻辣烫摊:“老板,每样都来一点。 ”老板提醒她那得五十块钱起步。 “嗯,每样都要。 ”
第二步,奶茶店:“要最贵的,加所有能加的料。 ”
第三步,烧烤摊:“这个、这个、这个,各来五串。 ”
第四步,煎饼果子摊:“加三个鸡蛋,两根火腿肠,所有酱都要。 ”
二十分钟后,她面前摆着一座根本吃不完的食物小山。 她坐下来,开始慢慢地、认真地吃。 品尝辣、甜、咸、香混合成的、陌生而令人晕眩的复杂滋味。
路人投来奇怪的目光。 是的,她在故意浪费。 她想证明的,仅仅是一个简单又沉重的权利:我可以选择错误的、过量的、不合理的。 我可以做“不应该”做的事。 因为在这里,没有人会阻止我。
吃到一半,她吐了。 在路边垃圾桶,把刚吃下去的东西全吐了出来。 边吐边哭。 不是为了浪费的食物和钱,是为了那个在平壤永远不敢这样想、更不敢这样做的自己。 自由的滋味,第一次以如此剧烈而生理性的方式,被她体验和确认。
四、 带着“病毒”回归
回国过边境时,海关人员检查她的行李,拿起一包韩国辛拉面。 “这是什么? ”“方便面。 ”“为什么带外国食品? ”“想给弟弟尝尝。 ”
海关撕开包装,仔细检查面饼和调料。 玉珍的心跳得很平静。她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。 但有的东西,仪器查不出来比如她知道,方便面可以有七种味道;爱情可以试穿后退货;深夜可以交易;记忆可以删除,但选择本身,一旦知晓,就无法逆转。
列车驶过鸭绿江大桥,她打开那包面,干嚼了一口。 很咸,很硬,并不好吃。 但她笑了。 因为,这是她的选择。 在无数可能中,她选择了这包最贵、最不适合干嚼、最可能被扣下的面。
饭桌上,弟弟问:“姐,中国什么样? ”
她放下筷子,看着弟弟年轻的脸,想起超市货架前的恐慌、删除照片时那片白、以及呕吐时的泪水。 最后她说:“多到你会不知道选什么好。 ”
父亲点头:“所以还是我们这里好,简单。 ”
母亲给她盛上雪白的、国家配给的米饭: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安心了。 ”
她吃了一口。很香,很软,很熟悉。 她知道,明天起,她又是平壤的金玉珍了。
但真的还能一样吗? 当一个人尝过了“选择”的滋味,哪怕它伴随着焦虑和痛苦,她还能够真正安心于那份被安排好的“简单”吗? 那份深夜点外卖的自由靠谱的配资平台,和删除记忆的权力,到底是一种解放,还是一种更精致的负担? 如果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只会面对唯一选项,那么突然面对七种方便面时,那十七分钟的恐慌,究竟是文明的进步,还是人性的陷阱?
启灯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云南炒股配资 手套就薄薄一层,真能起到防护作用吗?
- 下一篇:没有了